科学教育方面,我们随便举出几件大事。早在1636年,英国牧师约翰哈佛已在波士顿创建了美洲第一所大学——哈佛学院,后来改为哈佛大学;1669年,担任英国剑桥大学教授的伟大科学家牛顿,发明微积分,发现万有引力定律,取得数学、力学、天文学方面一系列辉煌成果;1701年,着名的耶鲁大学在北美洲纽黑文诞生;1755年,俄罗斯莫斯科大学建立;1780年,美国科学院在波士顿成立;1784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成立……
所有这些了不起的人类文明成果,中国全部茫然不知。统治者只顾把维护和加强专制统治作为第一要务,不断制造文字狱,查禁图书,采用种种严厉手段禁锢思想;知识分子只好匍匐于极端专制统治的淫威之下,背四书五经、做八股文章、避文字之祸。专制统治将我们这个民族的大脑洗成白痴,中国岂有不落后挨打之理!
五、文字狱的野蛮性质和巨大危害
从数不胜数的文字狱中可以看出,中国封建专制时代,文网极端严密,思想禁锢极其厉害,这是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和落后于西方的重要原因之一。文字狱是专制制度的产物,它和我们前面谈过的科举制度都是为了禁锢思想、维护专制统治,但方法手段不同。如果说科举制度是“胡萝卜”,那么文字狱就是“大棒”。文字狱对中国社会的巨大危害,应该看作是极端专制制度的巨大危害。
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专制政治是灵魂,文字狱是专制政治的产物和具体表现,也是维护专制统治的手段。它伴随君主专制制度而产生,并与君主专制制度成正比发展。明清时期,中国君主专制主义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文字狱也达到空前兴盛的地步。所以,文网之密,处刑之重,范围之广,近代超过古代,就像明清的君主专制程度超过秦汉一样。
文字狱打击的主要对象是知识分子。中国封建时代的知识分子,作为贵族与平民的中间阶层,既可以进入统治集团,为专制统治效力;也可以沦为被统治者,用文字批评朝政,甚至鼓动民众造反。所以,历代统治者总是采取恩威并重的两面政策,一面用高官厚禄引诱;一面用血腥屠杀威慑。而对知识分子血腥屠杀的借口便是文字的禁忌——在对方的文字中找罪状、兴大狱,以树立君主绝对权威、维护专制统治。中国专制君主的权力始终不受限制,所以能够任意杀人,而文字狱只是君主杀一儆百、铲除他所不喜欢的臣民最方便的借口和手段。
由于专制统治者对文字狱很感兴趣,有告必查,所以一些不逞之徒故意摘引仇家文字,借以报复私仇;甚至自制犯禁文字,填上别人名字,栽赃诬陷,以图敲诈勒索,如果遭到对方拒绝,便向官府直至朝廷告发,致使诬告之风盛行,坏人乐不可支,好人提心吊胆,人人自危。
文字狱案件不同于一般刑事案件。一般刑事案件,总是先有犯罪嫌疑或行为,然后据以判处,绝大多数不判死罪。而文字狱案件往往是先有特定的铲除对象,该铲除对象又没有任何罪行,于是就挑剔他的文辞细故,从中查找罪证,且每一文字狱都被定为“叛逆”、“诽谤”性质的政治案件,绝大多数要被判处死罪。
文字狱案件几乎都是冤假错案,罪名是从作者的文字中深文周纳、无限上纲、百般罗织而成的,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词”。文字本是无罪的,只是“有罪者”的文字才会“有罪”,因而才构成文字狱。统治者今天看这个人顺眼,这个人的文字就没有问题;明天看这个人不顺眼了,这个人的文字中就有一大堆问题。我们以上讲述的大小文字狱,纯属曲解文意、吹毛求疵的冤案。统治者硬要给人寻找罪名,不管你多么小心谨慎,要想规避幸免,简直不可能。只要是笔下写出来的——大至几十本的专着文集;小至一篇短文、一封书信、一首诗甚至一个字、一句成语的断句,以及戏曲、音乐、绘画、图章等等,凡是与文字有关的,不论是自己创作的,还是传抄别人的、甚至传抄古人的,一经挑剔,都可以作为文字“诽谤”的罪证。
文字狱“案犯”遭受的刑罚是极其残酷的。一旦陷入不可理喻的文祸,总是被逮捕、抄家、坐牢、受审、重判,许多名人志士因此而蒙难。除了一小部分“幸运”的正犯被判终身监禁、流放充军之外,绝大多数惨遭斩首挖心、碎剐凌迟之祸!如果“案犯”早去世了,不免还被挖开坟墓、剖棺戮尸。而且一人得祸,株连极广,所有亲属家族,不管知情与否、识字与否,都得“从坐”甚至满门抄斩!只要稍与“案犯”沾边就会受到株连,一案动辄逮捕数百人。其实,清代并没有惩治文字犯罪的正式法律,但有“大逆”罪的判例。遇到文字狱,就援引“与大逆无异”定罪。(张友鸾《封建统治下的文字狱》,载2005年第6期《炎黄春秋》,第77-79页)“凡谋反及大逆,但共谋者,不分首从,皆凌迟处死。(正犯之)祖父、父、子、孙、兄、弟及同居之人,不分异姓及伯叔父、兄弟之子,不限籍之同异,年十六以上,不论笃疾、废疾,皆斩。其十五以下及(正犯之)母、女、妻、妾、姊、妹,若子之妻、妾,给付功臣之家为奴,财产入官”。(《大清律例·刑律》卷23,《中华律令集成》清卷,吉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5页)文字狱一旦构成,就意味着血淋淋的灭门惨祸即将发生。所以一人被捕,常常举家自杀,以免遭受酷刑,身首异处。之所以如此残酷,就因为专制统治者完全拥有以个人好恶决定别人命运的无限权力,可以随意杀人!
文字狱的罪恶是显而易见的。几千年来,中国封建统治集团为了维护其专制统治,极力压制言论自由。从焚书坑儒的秦代,到极端专制的明清,文字狱愈演愈烈,先进的思想文化不断遭到摧残,民族为之失去活力!就连鲁迅先生也作诗感慨说:“弄文罹文网,抗世违世情。积毁可销骨,空留纸上声。”(鲁迅《题〈呐喊〉》)谁能肯定文字狱不是阻碍中国历史发展进步的重要原因?
世界进入18世纪,西方各国已经先后摆脱封建制度束缚,走上资本主义道路,政治、经济、科学、技术迅猛发展。而中国强势的极端专制制度,始终有力量蛮横地推行文化专制主义政策,利用文字狱等极端手段,消除异端、禁锢思想、罗列罪状、滥杀无辜,以维护专制统治,结果造成举国“万马齐喑”的僵死局面,宁不阻碍社会发展进步?
专制统治者毫无理性的严密禁忌和血腥恐怖之下,全社会思想受到禁锢,人文精神几乎泯灭,民族灵性日渐丧失。明末文人张岱抨击说:“有明一代,国史失诬,家史失谀,野史失臆。故二百八十年,总成一诬妄世界。”(张岱《石匮书自序》)而“有清一代”更是每况愈下,洵如晚清文人龚自珍所言:“避席畏闻文字狱,着书都为稻粱谋。”(龚自珍《咏史》)由于文字之祸过于普遍和严酷,知识分子小心翼翼,竟然“以文为戒”,不敢发表见解;做学问只好把功夫用在远离现实政治的考据学上,不敢过问现实;与人交谈,互相戒备,只说无关紧要的废话套话,不敢涉及政治,生怕一不小心触犯忌讳;酒店茶馆大书“莫谈国事”,唯恐祸从口出、殃及全家。难怪国人变得麻木,遇事只当“看客”,中国社会能不落后吗?
在这种极端严密、恐怖的思想言论禁锢之下,文人读书做文章动辄惹来杀身之祸,从此胆怯了,也学乖、学聪明了,遇事少说为佳,不敢关心国家大事,只好纵情声色,放浪形骸,麻醉自己,远离现实,丢掉气节,俯首为奴,其思想、智慧、胆识和创造力受到严重束缚。即使说话写东西,也只能歌功颂德、粉饰太平,中国的传统文化因此变成不折不扣的奴才文化!
奇怪的是,时至今日,人民当家做主,而奴才文化竟然大行其道!银屏之上,一场场“皇上英明、臣罪当诛”的正面大戏滚滚而来,直让专制时代再现辉煌!更有轻佻学者论史,故作“宽宏大量”风度,每以“能够理解”为辞,公然替封建专制帝王的罪恶辩护,是非颠倒,漠视民意,业已引起公众强烈愤慨。
例如,被掌掴的某学者在电视上侃侃而谈,竟替罪恶的文字狱屡屡辩护说:“文字狱有它的历史局限性,虽然制约了一定的思想灵性,但起码维持了社会稳定。”“康熙帝亲自处理的《南山集》案,和四辅政大臣处理的‘明史’案相比,略为理性,略为慎刑,体现了康熙帝为政以宽、为刑以慎的特点。这主要表现在漫长的处理过程,最后还是理胜于情、法胜于理,仅处死戴名世与方孝标(已死剉尸)两个人。这样一来,‘得恩旨全活者三百余人’。康熙末年的这件文字狱,比起初年的庄氏史案,实在‘格外开恩’,处罚很轻了。康熙帝不想得罪更多的汉族知识分子,也借以表现他个人的威中有恩”。(阎崇年《康熙大帝》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211页)他还说:“大兴‘文字狱’是不好,受到了激烈的批评。但是,雍正的这一做法对于清王朝国家的统一、减弱诋毁政权还是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见赵武明《满学专家破解清史“疑案”本报记者独家专访阎崇年》,载《兰州晚报》2005年10月20日A27版)这些话充分肯定了文字狱的巨大历史“功绩”,赤裸裸为文字狱歌功颂德!真不知以文字狱手段冤杀无数知识分子的康雍乾们地下有知,将会如何厚赏我们的奴才学者!
林语堂先生曾经感慨说:奴才本身就处在社会的最底层,利益每天都在受到侵害,却具有着统治阶级的意识,要在动物界找到这么愚蠢的东西几乎不可能。文字狱作为知识分子挥之不去的千古梦魇,任何时候都是野蛮政治的手段,而不是文明政治的表现;任何时候都只对专制统治有利,而对民族发展进步事业是巨大灾难,岂能为之大唱赞歌?现代民主、法制和人权制度是防止一切专制政治及其文字狱、保障人民享有充分民主自由与合法权益的唯一正确途径。我们的文化历史学者应该为此呼吁,而不是相反。
 微信赞赏
微信赞赏 支付宝赞赏
支付宝赞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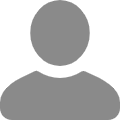












最新评论
exyeuer 在《“人口红利”概念的邪恶之处》上说:
henry 在《日本开发出一种抗衰老疫苗》上说:
匿名用户 在《2015年,马云湖畔大学,一个极其危险的政治信号》上说:
焦点新闻 在《美国女模特戴特朗普面罩呼吁粉丝投票》上说:
匿名用户 在《“鼓励农民进城”是一个大骗局》上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