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凡一个王朝积弊已久,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统治集团和普罗大众之间必定是离心离德,势如水火,双方利益上冲突,观念上对立,呈现此消彼长、你死我活的零和博弈状态。
万历年间的晚明就是如此,统治者颟顸无能,社会危机四伏,吏治腐败,民生艰难,已是风雨飘摇,积重难返。尽管有东厂西厂的秘密警察、特务机构制造恐怖,有锦衣卫的暴力机器勉强维持,也不过是百足之虫苟延残喘,由死而僵的耗日子。
中国人的耐性号称世界之最,只要不到活不下去的地步,断不会揭竿而起,但并不代表不会有不满,不平则鸣,有压迫就有反抗,有谎言就有不同的声音,打压与钳制日甚,反抗和不满也必然从自发走向自觉。
王朝末期,舆论上的万马齐喑基本已是奢望,当然也不会自愿退席,还民间一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双方力量对比很是微妙:庶民一张嘴,官字两个口,统治集团具备话语权上的巨大优势,但彼时统治者既已丧失了新朝肇始时期的强力控制,又缺乏广集民智从善如流的诚意和自信,于是就只能自说自话,虚与委蛇。而民间舆论则秉持反叛的凌厉武器,占据了天然的道德制高点,以毋庸置疑的正义性穷追猛打,正所谓众口铄金,积毁销骨,千夫所指,无疾而死,展开了对真相和话语权的猛烈争夺。
然后就出现了戏剧化的热闹场面:天圆地方,青红皂白,按道理凡事的非曲直不难判断,朝野却各弹各的曲,各唱各的调——民间喜爱的、支持的、追求的,朝廷几乎发自本能的反对、限制、打压;而朝廷所褒扬的、提倡的、坚持的,民间更是毫不留情的加以嘲讽、揶揄、唾弃。结果就是官方说东,民间指西,官说清廉,民骂贪墨,官方说他是人才,民间谓之蠢货,官鉴定是真老虎,民间论证是纸糊的。纷纷扰扰,莫衷一是,针锋相对,无法调和。
面对如此诡异的局面,首辅王锡爵困惑不已,向当时供职吏部,后来创立东林学派的大学者顾宪成抱怨道:“当今所最怪者,庙堂之是非,天下必反之。”现在怎么这么邪性,朝廷的是非判断,全天下必定要反着来。老爷们定下的调子,屁民们为啥不买帐了呢?一个个吃饱了没事干,指手画脚的唱反调,这是怎么回事呢,顾大人?顾宪成要言不烦,只硬邦邦地回了一句:“吾见天下之是非,庙堂必欲反之耳。”屁股决定脑袋,您是首辅,俺是草泥马代言人,所以在俺看来情况恰恰相反,是天下人的是非判断,庙堂之上的硬要颠倒过来罢了!
顾先生堪称真正践行民本思想,密切联系群众的先进代表!不错,朝野对立,是非满拧,但因果关系要搞清,错不在天下人,而在于庙堂之上。用《三国演义》中的话,现如今已是庙堂之上,朽木为官,殿陛之间,禽兽食禄;狼心狗行之辈,滚滚当道,奴颜婢膝之徒,纷纷秉政。以致社稷丘墟,苍生涂炭。都烂污成一坨臭狗屎了,还要腆着脸说自己伟大光荣正确?皇帝愚蠢到光屁股出镜了,还要屁民山呼万岁,称赞你衣服华美,巧夺天工?你有罔顾民意睁眼说瞎话的人格分裂症,俺可好好的呢,不是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既不会爱上你,更没有配合你撒谎的义务。
朝野关系紧张,舆论上打嘴仗,归根结底还是个利益问题,正因为有了双方的利害冲突,才有必要分清楚个子丑寅卯。是非观是个大是大非的立场问题,如同晋惠帝要田里青蛙分清到底是为官乎,为私乎一样,围观者要挨个站队表态。过程就像赵高的指鹿为马,事实摆在眼前,结论却截然相反,不要相信自己的眼睛和经验,必要的话,寡人可以找一百个专家来论证这个生物是马非鹿的科学依据,还可以找一千个御用文人含泪劝告广大不明真相者,要和谐,要感恩,不要再纠缠马和鹿的问题,那些匈奴啊六国余党啊等等别有用心的一小撮正在等着我们做错写什么呢!如果还不听劝告,对不起,你只好闭嘴了,于是就有了腹诽与止谤、防民之口和道路以目,直至人头滚滚的文字狱。
万历的舆论对立发展到天启年间,终于演变成了极端形式的高潮,熹宗义无反顾的开动暴力机器,将反对者予以肉体上的消灭。不过杀人者忘了,刘项原来不读书,闷声的不一定都想发大财,不许放屁的结果是火山爆发。历史公正而又无情,武力清场刚过20周年,还算勤勉政务的继任者,末代皇帝朱由检,就绝望的自缢在了煤山。
此时,山下已是洪水滔天。
来源:http://blog.sina.com.cn/s/blog_45ff42150100e5r9.html
赞赏 微信赞赏
微信赞赏 支付宝赞赏
支付宝赞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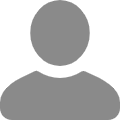












最新评论
exyeuer 在《“人口红利”概念的邪恶之处》上说:
henry 在《日本开发出一种抗衰老疫苗》上说:
匿名用户 在《2015年,马云湖畔大学,一个极其危险的政治信号》上说:
焦点新闻 在《美国女模特戴特朗普面罩呼吁粉丝投票》上说:
匿名用户 在《“鼓励农民进城”是一个大骗局》上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