惩罚的手段并不只是像水浒里对着犯人重打一百杀威棒,更多的是凭借公权侵犯他人消极自由,制度上造成的不平等,无视普遍的政治价值以及可能造成的与自然偶然性毫不相干的良好愿望无法得彰。
张宪超|文
希腊神话中主神宙斯的儿子坦塔罗斯,由于侮辱众神受到被绑在河水中央的惩罚。河流的上面长着果树,对此并不存在任何的优待,相反,对他的惩罚是极为深刻的,坦塔罗斯想喝水时河水马上退去,想吃果子时立刻刮来一阵风。
坦塔罗斯的痛苦在于,看见目标却永远达不到目标。
不去讨论坦塔罗斯的错误在于什么,从对他的惩罚能够看出,愿望与满足愿望而不得之间的残酷,表现在他的身上就是承受巨大的痛苦。不管是作为一种惩罚的手段,还是生活中捉弄他人的惯用伎俩,都存在一个分明近在眼前却又得不到满足的事实——愿望永远得不到满足。
无论怎样,作为被施展的对象,幸福感即便再低,恐怕只能是奢望。
托克维尔说,“社会稳定的威胁来自于愿望和满足愿望之间的张力,如果仅仅是满足愿望的机会有限还不足畏惧,最可怕的是愿望已经被挑起了胃口,而现实的机会却非常之有限,这样的情形就只会让局势日益恶化。”
托氏这番话,丝毫不危言耸听。
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应允的承诺如不及时满足,即便是朋友间,也会种下不和谐的种子,不至于到破裂的边缘,至少不信任和猜忌的情绪会日益高涨。如若一个人的作风一贯如此,最终必然会到达一个临界点,从现实来看,这种结果往往是最坏的。
如果存在一种角色,可以任意插足不同的行业,把个体本来获得最大的报答向下拉至极低,这样的社会按照柏拉图的解释就是不正义的。因为在他的理想国中的正义,是每个人必须在国家里执行一种最适合他天性的职务。
换句话说,就是各归其位各司其职。对于一个开宗明义一切为公的组织来说,选择最适合他天性的职务似乎更为关键。
在消极自由受到严重侵犯的极权社会里,掌有公权力意味着囊括一切,一个绝对的威权统治。与此同时,私人空间几乎被压制到最低,更不可能会有“公民不服从”的意志对政权构成制衡。
社会秩序完全由国家权力控制,窃以为也就意味着,被挑起的胃口同时得不到满足的可能增加。即便人人沉默,到了生存堪忧的境地,会出现绝处逢生破釜沉舟的“奇迹”。
对于同样的问题,在一个公权受到制衡的社会,存在着多种形式的妥协,公民的愿望与满足愿望的可能,会商量着来,极力弥合它们之间的张力。政府与公民彼此遵循的是一种确定的规则——法律。他们在不同的职业中拓展出一种共识,这种共识随着时间推移得到强化。
我非常认同18世纪的一位政务家说的,英国未成文宪法是这样产生的:“一些由某种急迫的权宜之计或私人利益所导致的偶然行为,随着时间的推移而结合起来并得到强化,从而成为习惯法”。以至于早在成文法律形成以前,它便受到了人们的尊重,并成为人们的行动指南。
从历史和现实来看,一个更有活力的也更为稳定有序的社会,依赖于不同的群体阶层互不干预以及在此基础上达成普遍认同的共识,更重要的是打开通向公民社会的门户。在这个意义上,稳定有序的社会是一个正义社会。
一种无法同自身政治任务相适应的社会制度,虽然会造成愿望与满足愿望之间的张力,甚至会导致极大的张力,但在生活中,广泛的有可能也会是自始至终的偶然因素,也会让二者处在极不相称的尴尬位置。
对于出生地这件事来说,我们是无法做出选择的,出生在首善之区和在不毛之地是很偶然的。问题在于,如果两个出身霄壤之别的人,在迈向独立的人的过程中受到不同程度的差别对待,在划分利益的时候是从起点处就对某些人更为有利,与此相对,就是另一部分人处在极为不利的境地。
为什么仅仅一河之隔,会出现如此严重的差异化?从入学到高考,存在普遍的不平等,同样作为适龄儿童,为什么不能在自己的国土上自由的入学、迁徙。大家都是有身份证的人,难道11开头的就要比12、13开头的金贵?如果按照这个逻辑追问下去会发现,从孩童到老人,生命中的各处路口,红灯绿灯总会有差异。难道自然的偶然性会是因为一条河在作祟?
对于个体来说,满足愿望付出成本的差异,更多的人把它归咎于六个字——人生而不平等。他们不相信生而平等是由现实的局面造成的。
事实上,差异化如此明显而即刻,制度上的不平等要远比生而不平等严重得多。若保障愿望得以满足,应尽可能地从平等公民的地位做出选择。
正如罗尔斯强调的,正义的主要问题是社会的基本结构,其理由是它的影响是极其深刻和广泛并自始至终……我们遵循的是这样一个观念:两个正义原则试图减轻自然的偶因和社会的机遇带来的任意影响。
罗尔斯的政治理想是建立一个“制度上保障所有人的自尊”的正义社会。个体满足愿望与否,归根结底在于制度上的保障,即便是不存在任意插足的势力,制度上无法保障公民合理合法的愿望得到满足,那也不会是多么正义的。
如果说自尊的社会基础被认为是最重要的基本善,那么每一个体会被预设为在追求这些善,问题在于,能否被从上到下的制度保障以及满足。从来最悲催的不在于自暴自弃,而在于空有一腔报国志,却无半个识才人。
当国家处于变革时代,任何体制以外的不确定因素都有可能成为阻碍进步的力量。个体对民族国家的认同,会由于民族的危机的日益严峻得到凝聚,两党间通力合作是大势所趋,由下层传递的呼声同样可能变成民族意志。
按照孔飞力先生的说法,真知灼见不可能只为权势力量所垄断,广开言路成为真正的历史进步。
与此相对,一个承平日久的社会,不存在以“救亡”为中心的民族主义诉求。何为良好的生活,似乎成为越来越多的人的追求和思考的问题,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追求幸福生活的美好愿望是一个常态的话题。
其实,无论是正义社会还是马格利特的正派社会理论,都只解决了“我们如何生活在一起”的问题,但没有回答“我如何能够过上美好人生”的问题,也就是幸福的问题。或许,这样的美好愿望与等而下之的基本诉求相比,就现实来看,有一些理想主义和不切实际,但追求美好生活何尝不是人们的权利。
在这个意义上,愿望并没有差别,关键就在于满足愿望的机会是否有限。一切的前提就是须在一个正义的社会范畴内,否则,不产生任何化学反应。
刻在雅典德尔菲神庙上的两句箴言:认识你自己,凡事勿过度。周濂老师这样解释,只有当人们真正认识到自己的潜能与限度,知道自己的应得,了解完成繁荣之后所可能获得的身份和位置,才可能坦然接受生活,不去逾越那永恒固定的界限。
我总觉得,我们在认识自己之前,有必要先了解自身所处的环境。
作为一种惩罚的手段,坦塔罗斯的痛苦,看见目标却永远达不到目标。倘若类似的痛苦被施展于一国之公民身上,惩罚者恰恰又是强权的执行者以及强权本身。
惩罚的手段并不只是像水浒里对着犯人重打一百杀威棒,更多的是凭借公权侵犯他人消极自由,制度上造成的不平等,无视普遍的政治价值以及可能造成的与自然偶然性毫不相干的良好愿望无法得彰。
每个时代从不缺乏优秀,问题在于是否有一个良好的上升渠道。科举制取代察举制是一个迈进,社会总不能长期被氏族大阀控制,底下的人难道不愿居于庙堂之高?
正义社会的目的,制度上保障所有人的自尊,尊严包括,权利、机会、自由、平等……在减轻自然偶因和社会机遇的任意影响之外,不要从制度上让人们留有遗憾。
换成罗尔斯的话,就是每个人都要被保障有一种平等的自由来追求他高兴的生活计划,只要这计划不违反正义的要求。否则,愿望与满足愿望无法保障在适度的范围内,张力伸展到极大时,只会让现存的局面日益恶化。
赞赏 微信赞赏
微信赞赏 支付宝赞赏
支付宝赞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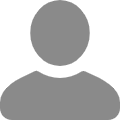












最新评论
exyeuer 在《“人口红利”概念的邪恶之处》上说:
henry 在《日本开发出一种抗衰老疫苗》上说:
匿名用户 在《2015年,马云湖畔大学,一个极其危险的政治信号》上说:
焦点新闻 在《美国女模特戴特朗普面罩呼吁粉丝投票》上说:
匿名用户 在《“鼓励农民进城”是一个大骗局》上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