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德国达豪集中营入口处,刻着17世纪一位诗人的警世名言:“当一个政权开始烧书的时候,若不加以阻止,它的下一步就要烧人!当一个政权开始禁言的时候,若不加以阻止,它的下一步就要灭口!”
清初顾炎武曾经沉痛地说过:亡国必先亡士。古代的“士”相当于现代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不仅代表国家的智力水平,也代表国家的精神高度。我们之所以不敢小瞧英国,是因为它产生了许多莎士比亚、牛顿这样的文学科学巨匠,它拥有一批牛津、剑桥这样的顶尖学府,它培养了许多卓然挺立傲然不群的杰出人士。我们之所以歌颂盛唐,是因为它产生了“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的李白,产生了“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杜甫,产生了“若世无孔子,不当入弟子之列”的韩愈,产生了敢写《卖炭翁》的白居易。回顾前辈,如在天际;反观自身,不胜嘘唏。前不久“倪萍们”的“共和国脊梁奖”,已经成为世界级的笑话,用钱去买“共和国脊梁奖”,恰恰证明自己早已没有脊梁!
倪萍们“共和国脊梁奖”暴光后,我连续写了三篇《倪萍印象》(之一、二、三),批评倪萍后接着又反躬自问:“我”有脊梁吗?“我们”有脊梁吗?谁敢说自己比倪萍更有道德优越感?如今,知识分子已经从人们尊敬的对象变成了人们嘲讽的靶子,“专家”已被大家讥讽为“砖家”,“教授”更被人们骂为“叫兽”。要是能看到大学里评职称时,读书人的卑微态度;要是了解每年评奖时,教授们到处求人的样子;要是得知为了争取到重大课题,很多斯文教授到处行贿的丑态:要是清楚教授和专家的许多论文,常常只是在为长官意志进行论证和辩护,我想社会大众更要向专家们脸上吐口水,更要朝教授们头上撒尿。包括我本人在内的很多“教授”“专家”,真的不值得社会大众尊敬,甚至我自己也瞧不起自己!
君不见前不久又在吹捧那个某人的延安甚么“讲话”吗?(胡风因置疑此“讲话”而入狱,并祸及近万人冤案),又在发动中囯精英文人签字吹捧“讲话”,其中竞有老右派王蒙、诺奖莫言!他们尚有灵魂否?签字者每人受赏人民币一千元施捨,穷疯了?中囯,可怜的中囯社会文化环境竟被“特色”改造成如雾霾一般令生者绝望。这民族还有救吗?对外打仗?儿女们会还会以生命去保卫这种文化家园吗?这个只属少数人私有的特权国家吗?
不过,中国知识分子绝非从来如此。很多知识分子在一九四九以前都有款有形有血有肉有棱有角,为人风骨凛然,说话掷地有声。想想刘文典面折蒋介石的傲气,想想张奚若在国民参政会上詈骂蒋介石独裁的刚烈,想想章太炎、黄侃师弟的狂傲,想想傅斯年骂倒孔祥熙和宋子文两任行政院长的勇敢,比起当年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些“民国范儿”真让读书人气畅神旺!
可是,绝大部分人一九四九年后,突然好像全都一夜抽去了脊梁,郭沫若先生的丑恶表演就不用说了,连潘光旦先生这样的硬汉也低下了高贵的头,而冯友兰先生这样“新儒学”的代表人物,也对儒家创始人孔子破口大骂。
1951年 全国“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其实就是让所有读书人自己当众打自己的耳光,自己当众吃下自己拉的屎喝自己撒的尿。潘光旦先生接二连三地写了十二次检讨,还在报纸上发表了上万字的长篇自我批判文章——《为什么仇美仇不起来》,把自己的父母、师长、同学、教育和科研逐一否定,完全是在当众自己打自己的嘴巴。想当年,潘光旦是民国时期的独腿硬汉,历任清华和西南联大教务长,从来不向权贵低头,从来不向命运服软,可是1949年后彻底否定自己,不断自轻自贱,不断自打嘴巴,那一幅卑微、顺从的模样让人不敢相信这就是昔日的潘光旦。潘光旦先生还只是求自己蒙混过关,更有不少人甘当当局的“密探”,不少人出卖自己的师长,很多人以为虎作伥为荣,这六七十年整个知识界真是斯文扫地,满地鸡毛!
比起那些卖友求荣卖师求官的小丑,潘光旦先生算是一位求饶但不害人的君子,可是,他当众掌嘴还是无人领情,一九五七年照样被打成右派,文化大革命中照样被打成“牛鬼蛇神”,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对好友叶笃义介绍了自己的“三S”求生经验——“Surrender(投降)、Submit(屈从)、Survive(生存)”,最后发现想做屈从的奴隶也没法活命的时候,他又补上“一个S”——“Succumb(毁灭)”。晚年以“三S” “投降”“屈从”还没有人接受,真像鲁迅先生说的那样“求当奴隶而不可得”,“Survive(生存)”无望,就不得不走向“Succumb(毁灭)”。当奴隶的资格也被剥夺,潘先生死得没有半点尊严。
是什么原因让民国时期的硬汉,变成甘愿“Submit(屈从)”以求“Survive(生存)”的熊包?为什么当年敢当面大骂蒋介石独裁,四九年以后“乐于”唾面自干?过去把面子看得比生命还重的知识精英,后来却活得如猪似狗没有一点“人”样?
从1951年“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开始,一直延续了几十年的政治运动。
第一步是让所有知识分子觉得自己毫无价值可言,过去学的知识全部是人类垃圾,而且知识越多越反动,知识分子不管是真心还是假意,他们都承认自己既“肮脏”又“无能”,对那个被神化的“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心悦诚服;
第二步就是摧毁知识分子的意志,让他们都以长官的意志为自己的意志;
第三步就是羞辱知识分子的人格,让他们不断自我检讨自我批判,自己把自己整得灰头土脸;
第四步是给他们诱以利饵,用官用钱用职称用课题来笼络他们,让他们像狗一样吃嗟来之食,于是就出现了目前这种“重赏之下必有懦夫”的局面。
任何一个人要是自己也觉得自己百无一能——既没有价值,又没有意志,更没有人格,一定会自己极度鄙视自己。像潘光旦先生这样的硬汉,最后以“投降”、“屈从”为手段,以“生存”为人生目标,在这六七十年中肯定不是个案和特例。他们活得非常屈辱,死得也非常窝囊,还谈什么气度,还谈什么风骨,还谈什么高傲!
读书人毕竟也是人,谁都不是特殊材料做成的,大多数人在面临死亡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是自己如何活命,想到的是如何保护家人的安全,比起自己和家人的生命安全,人格、风骨和尊严都不值一提。从公认的“铁汉”到公开的“投降”,潘光旦完全像换了一个人似的,由此我想到了哈耶克的《通向奴役之路》,由此我想到了教育学中所说的成长环境。在一个极不健全家庭中长大的孩子,他们的人格也会极不健全。养成知识分子铮铮铁骨需要特殊的外部条件,如果有风骨的人被剥夺了生存权利,如果说真话的人会掉脑袋,谁还有什么风骨?谁还敢说真话?我决没有嘲笑潘光旦先生的意思,更没有嘲笑潘光旦先生的资格,如果我处在潘光旦先生同样的环境中,我肯定比潘光旦先生更早地举起了白旗。
别提什么“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警句,别说什么“宁可站着死,绝不跪着生”的格言,当你自己可能坐牢掉脑袋,当你的家人可能被牵连,这些格言统统都会抛向九霄云外,除了极少数人可能宁折不弯,大多数人的第一需求就是生存需求,在文化大革命那种残酷荒唐的岁月,潘光旦先生以“Submit(屈从)”来求“Survive(生存)”,并不奇怪,更不丢人。民国时期之所以那么多人敢骂蒋介石,是因为多数人骂了蒋介石没有多大的风险——由于能骂,所以敢骂。
把潘光旦这样的一条硬汉,活活给整得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我不知道这是国家的胜利,还是我们民族的悲哀。如果一个国家不能容忍一条硬汉,举世全是阿谀奉承吹牛拍马的喽罗,怎么能宣称“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呢?
大家沒忘记民国时期被关在上海监狱中的“七君子”吧,到了毛时期,以其中之一的史良为例,她这“君子”就变成了小人,在压力下,行努力揭发、告密朋友之能事。
摧毁一条硬汉的人格和尊严,可能就摧毁了一个民族的人格和尊严,这是极端的无耻、丑恶和可怕的犯罪!
如果一个国家把所有人的脊梁全都抽掉,如果一个国家里大部分人都是奴才,如果一个国家所有人只懂得“听话”,如果一个国家所有人只知道磕头谢恩,我不明白这叫什么“盛世”?我更看不出这叫什么“英明”?
文/戴建业
赞赏 微信赞赏
微信赞赏 支付宝赞赏
支付宝赞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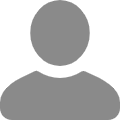












最新评论
exyeuer 在《“人口红利”概念的邪恶之处》上说:
henry 在《日本开发出一种抗衰老疫苗》上说:
匿名用户 在《2015年,马云湖畔大学,一个极其危险的政治信号》上说:
焦点新闻 在《美国女模特戴特朗普面罩呼吁粉丝投票》上说:
匿名用户 在《“鼓励农民进城”是一个大骗局》上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