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房地产市场遍试各种药方后,人们突然发现,早在1998年房改时,正确的药方就已经存在。《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国发〔1998〕23号),是中国改革史上最伟大的文件之一。文件中提出的“停止住房实物分配,逐步实行住房分配的货币化,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房为主的多层次城镇住房供应体系,对不同收入家庭实行不同的住房供应政策,最低收入家庭由政府或者单位提供廉租住房,中低收入家庭,购买经济适用住房,其他收入家庭购买、租赁市场价格的商品住房”,几乎可以原封不动地用来作为今天的房地产“新政”。中国房地产龙头企业老总郁亮在接受采访时说:“我觉得这次房地产行业的调控,有点像回到1998年左右。”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后来为什么偏离了国发〔1998〕23号文?这个问题不搞清,即便今天回到1998年房改政策,也不能保证不会再次出现偏离。
二
回顾1998年以后的房地产市场的演进,与23号文偏离最大的,就是“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房为主的多层次城镇住房供应体系”这一条--本应“为主”的经济适用房完全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以商品房为主的住房供应体系。在我看来,主要原因有两个,一个是客观的,一个是主观的。
客观原因,就是市场套利。
房改初期,商品房和经济适用房价格差别不大,加上申请资格和上市期限的限制,两者之间的价格差不足以诱发大规模套利。但随着商品房价格的上升,与经济适用房的价格迅速拉开。经济适用房较短的“解禁期”已不足以抵消两个市场套利的巨大利益。于是,由“人”来决定如何分配的经济适用房,成为诱发腐败的巨大温床。
中国商品房市场的设计,从一开始就是为了融资。1990年代初期,为吸收超发的货币,对抗通货膨胀,先后建立起股票、期货和不动产三大资本市场。房地产市场就是资本市场。1998年房改如同大规模城市“上市”,使房地产一举超过股票、债券,成为中国地方政府最主要的资本来源。当套利迫使地方政府在“住”(经济适用房)和“炒”(商品房)之间只能二选一的条件下,地方政府本能地选择了更为重要的资本市场。
主观上的原因,就是将商品房视作“市场”,同时把经济适用房贴上“计划”的标签。在改革的大背景下,不断增加“市场”,减少“计划”,乃至最终“让市场起主导性/决定性作用”,已经成为政策制定者的信条。经济适用房和商品房之间出现大规模套利后,一个本能的判断,就是市场和计划双轨制必须“并轨”--“市场”的商品房和“计划”的经济适用房中只能二选一。显然,本拟作为供给主体的经济适用房,首先会被政策抛弃。
三
今天,我们面对的依然是类似的问题:1、商品房市场和保障房、廉租房、租赁房市场之间的套利;2、如何设计非价格决定的政策性住房的分配机制。
由于作为资本市场的房地产涉及太多人的利益,地位很难动摇,一旦出现不同市场间的套利,就一定会再次给商品房市场让路。最近,一些城市打压商改住、SOHO改住、农房改住,以及拆违、打压小产权等,本质上,都是在打击市场套利,维护资本市场的价值。这意味着,如果这两个问题不解决,住房供应市场就一定会再次回到单一不动产市场。在单一住宅供应体系下,所谓的住房政策,就只能是简单的供给数量管理。
显然,我们今天的政策并非简单回到1998年房改那么简单。只要不能设计出区分不同市场的制度,“以经济适用房为主的多层次城镇住房供应体系”就依然会是一句空话。自1998年以来住房市场的演变告诉我们,如果要建立“多层次的住房供应体系”,首先必须建立起使不同层次住房供给模式间无法套利的住房制度--如果没有渠道,不论水量多少,都不会流到缺水的农田里。
结论很清楚,当下住房政策的核心,不是干预市场上的房价或供给规模,而是建立无法互相套利的多样化的住房市场。
四
回到“以经济适用房为主的多层次城镇住房供应体系”,第一个要做的,就是定义政策性住房的准入资格。这是区分“住”和“炒”两个市场的关键。原来的经济适用房准入资格与单位挂钩,然后拓展到与户籍挂钩。但当“新市民”成为城市住房需求主体时,这一准入标准就很难与真实需求相匹配了。
为什么经济适用房要与户籍挂钩?这就涉及到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交易模式问题。
在发达国家,主体税种是直接税,纳税人相当于城市公共服务购买人,无论有没有户籍,只要纳税,就有权享受公共服务。在中国,由于缺少直接税,如果给所有人提供公共服务,必定会出现空间套利行为--人口从公共服务较差的城市向公共服务较好的城市迁移。最终,公共服务水平较高的城市会因为吸引过多人口而入不敷出。这就是多城市的中国与单一城市的新加坡,在住房保障制度上面临的最大条件差异。
五
在现有的人口甄别工具中,只有户籍可堪一用。如果以户籍作为政策性住房的准入前提,政策性住房(及其相关的公共服务)就一定会福利化。户籍价值上升,取消户籍制度就更加困难。而福利化的住房制度,也就不可能实现“广覆盖”。
在没有直接税的条件下,突破户籍制度的一个办法,就是将同户籍挂钩的保障性住房的申请资格,转为同就业挂钩。具体讲就是只要缴纳“五险一金”,就有资格申请政策性住房。其政策结果,就是户籍贬值,“五险一金”升值。由于中国是间接税为主,对就业的补贴,就会通过在地企业竞争力的提高,转变为政府的税收增加。1998年时,“五险一金”制度远没有今天完备,而今天,全面覆盖的“五险一金”完全具备替代户籍制度的可能。
一旦政策性住房不是同户籍而是同就业挂钩,其福利性质立刻就会改变。因为低房价会通过企业劳动力成本降低获得额外竞争力,并导致全社会税收的增加。
六
同户籍相比,就业具有很高的流动性。在多城竞争的环境里,就可能出现空间套利--在不同城市就业套取政策性住房的资格。现在普遍推行的办法,就是政策性住房只租不售。这个办法看似解决了空间套利的问题,但实际上是以社会资本损失为代价的。假设一套市值100万的住房,只租不售,这100万市值就只是“影子价值”--既不属于个人,社会也得不到。由于不能流通,这100万社会资本在经济体系里无端消失了。
在租赁为主的市场,公共服务改善带来的土地升值,既不能转化为社会资本,也不能带来个人财富的增加--社会投入的资源(土地、公共服务、建安)不变,但形成的价值却大为缩水。这就是为什么改革开放前纯租赁的公房制度下,全社会资本不足,社会财富积累效率低下。
更为严重的是,只租不售会固化社会的贫富分层。1998年房改到现在,城市居民已经分为有房的居民和无房的居民两大阶级。社会财富的一个主要的分配形式,就是通过改进公共服务推高不动产所有者物业价值。这一财富转移机制,使得无房居民的财富很难赶上有房居民。而且只要公共服务改善,住房就会继续升值,进入有产阶级的门槛就会升高,社会贫富差距就会进一步加剧。
怎样既能防止套利,又能避免贫富分化?这还是要回到1998年经济适用房制度设计存在的套利问题。经济适用房之所以能被用来套利,第一是时间太短,第二是分配不公。如果加长“解禁”期限,同时规定一个人一生中都有权获得一次(并且只能有一次)政策性住房,再辅之小户型设计等,就可以有效地将政策性住房与商品房市场有效区隔。
正确的政策住房供给制度,既不能是只售不租,也不是只租不售,而是两者的结合--“先租后售”。首先,将住房租给新就业城市居民。然后将房租积累到个人账户。一定年限后,补足成本差价后,获得完整的商品房产权。由于劳动力有随着时间“折旧”的特点,只要解禁时间足够长,空间套利的可能就变得很小。
更为重要的是,由于解禁后的政策房可以上市,因此可以成为合格的抵押品在资本市场上融资——政府无需为解决住房问题沉淀大量流动资金。而这一点恰是改革开放之前,住房只能覆盖少量居民的根本原因。
七
有区别才有政策。一旦有了不同的住房供给渠道,我们就可能有针对性地对不同层次的住房“精确”供地。由于政策性住房与城市的真实需求正相关,因此,可以作为其他层次住宅的供地的锚。政府通过调整不同住房和政策性住房供给的比例,可以影响城市扩张的速度。比如,规定每建设10平方米保障住房,可以在商品房市场上推出1平方米住房,来调节城市在资本市场上融资的规模--城市扩张速度快,商品房可以增加到2平方米;城市扩张减慢,需要去库存,就减少到0.5平方米,甚至暂停商品房供给。
当城市建成后,商品房市场主要的作用,就不再是融资,而是通过交易给没有流通的不动产定价,从而创造信用。一级土地市场上的商品房供地需求,也就随之大幅减少。
住的市场(保障住房)和炒的市场(商品房)分开后,房地产市场就可以重新设计差异的政策--在商品房市场,大幅度减少供地(为防止高估值的不动产市场无预警崩盘,甚至可以暂时冻结市场交易);在保障房市场,则大力增加供地,有需必供,住有所居,实现城市基本住房全覆盖。
同1998年不同,那时城市住宅绝大部分都需要靠增量解决。而今天,通过增量形成“多层次城镇住房供应体系”的机会已经失去。现在只能设计不同的制度,将社会上的存量住房改造为“多层次的住房供应体系”:1、对于现有的保障性住房,可以通过“共有产权”的方式,将价格还原到购房时刻,然后按照“增值共享”的规则,转让给现有的住户;2、城中村等“小产权”住房,则可以通过每年交地租的办法使其合法化,成为租赁市场的主要组成部分;3、对空置房屋征税,将闲置商品房逼到租赁市场。通过针对存量住房制定不同的政策,就可以在存量基础上,重建多层次的住房体系。
八
1998年后地方政府转向商品房而不是经济适用房,还有一个为很多研究所忽视的问题,就是地方政府缺少足够的供应经济适用房激励。
新加坡政府为什么有强大的建设公共住房激励?不是他们的政府更亲民,而是因为低成本住宅会压低新加坡劳动力成本,其收益会从企业税收和就业增加带来的好处中收回。新加坡只有一级财政。整个国家像是一个独立核算的公司。收入从税收体现还是地价体现,对于政府而言是无差异的。
但中国目前税收制度,相当于联邦制国家--公共服务由地方政府提供,中央却获得税收大头。地方政府大规模建设政策性住房,带来的税收增加却须和中央财政分享,其本质就是牺牲卖地的溢价收益补贴中央财政。因此,地方政府一定会以地价方式而不是税收方式获得土地收益。显然,如果不能通过税制改革或转移支付,地方政府就会陷入公共住房提供越多,未来的公共服务负担越重的负面激励。
九
1998年房改在中国改革史上的意义,现在无论怎样称赞都不为过誉。可以说没有当初的房改,就没有今天中国的经济。但同时,由于缺少区隔不同市场的制度设计,导致大规模套利,最终没有建立起“以经济适用房为主的多层次城镇住房供应体系”。今天,如果我们要回到1998年房改的初衷,就必须补上“市场归市场,保障归保障”这一课。没有制度配合的政策,不是真正的政策,顶多算是美好的愿景。这就是我们从1998年房改得出的教训。
(作者为厦门大学教授)
赞赏 微信赞赏
微信赞赏 支付宝赞赏
支付宝赞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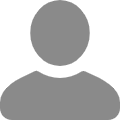












最新评论
exyeuer 在《“人口红利”概念的邪恶之处》上说:
henry 在《日本开发出一种抗衰老疫苗》上说:
匿名用户 在《2015年,马云湖畔大学,一个极其危险的政治信号》上说:
焦点新闻 在《美国女模特戴特朗普面罩呼吁粉丝投票》上说:
匿名用户 在《“鼓励农民进城”是一个大骗局》上说: